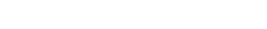二十个鸡蛋
王小平
1978年秋,我和另外九名同学被山外的中学录取,成了曲龙乡第一批走出去的初中生,那年我十二岁。
母亲怕我一人在外无人照应,也希望老师在学习上能给予我特别关照,便想着给老师送些心意。
那时还是集体生产,家家日子都像攥紧的拳头,吃穿用度全靠精打细算、从牙缝里省,连买油盐的钱都得从鸡窝里一点一点攒出来。家里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,可母亲为了实现这个朴素的愿望,竟悄悄攒下了二十个鸡蛋。她用谷糠垫着,锁在柜子里。
一个周末回家,母亲让我把鸡蛋带去送给老师。我不肯——那时候学生给老师送礼,是要被同学笑话的。母亲便又劝又吓,我终究拗不过她,只得极不情愿地把鸡蛋带回了学校。
住校生每人有一口木箱,放些换洗衣物和口粮。我把鸡蛋藏在米袋里,一直没敢拿出来。一间寝室住二十多人,我又生性胆小,更怕被人知道后嘲笑,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把鸡蛋送出去,一个月过去了,鸡蛋还在箱底压着。鸡蛋不再只是鸡蛋,它成了我青春初期一个秘密的沉重包袱。
有一天舀米时,我闻到一股异味,轻轻拨开米粒,竟看到鸡蛋上爬出了细小的蛆虫。我不敢声张,之后每次开箱关箱都像做贼,心理负担一天比一天重。直到放寒假,我编了个谎话,说寝室木箱忘记上锁,得回学校一趟。我翻山越岭几十公里,偷偷溜进空荡荡的寝室,将那二十个已经腐坏的鸡蛋扔掉了。
那一刻,压在心上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许多年后我才明白,落下的不只是石头,还有一个少年对世界非黑即白的判断。
我曾在心里暗暗埋怨过母亲的“固执”,也怜悯过她的“笨拙”。直到我自己也成为那个笨拙的人,在另一个崭新的时代里,用另一种方式不知所措地爱着我的孩子。
原来时间才是最慈悲的老师。它让我终于听懂:母亲送的从来不是鸡蛋,是一个农村人能拿出的全部尊严;我扔掉的也从来不是鸡蛋,是一个少年还无法承载的深情。
现在回想,那时的老师对待每个学生都如同自己的孩子,淳朴而公正。母亲的举动,源于她那份最简单、最深厚的期盼——天下父母,谁不盼着自己的孩子能被多看一眼,多一份出息呢?只是她不曾想到,这件在她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,却让少年的我忐忑不安地捱过了大半个学期。
如今,我的孩子也已到了当年我背着行囊出山的年纪。世界早已不是那个需要从鸡窝里攒攒凑凑才能表达心意的年代了。可每当看到他轻快地奔向更广阔的天地,我总会想起母亲锁进柜中的那二十枚鸡蛋——它们曾那么滚烫地压在少年的心头,如今却只余温润的光泽。
原来,每一代母亲都曾捧出过自己的“二十个鸡蛋”。形式各异,轻重不同,有时甚至成了孩子甜蜜的负担。但当我们穿过岁月回头望去,才会懂得:那些不知如何是好的爱,那些生怕给得不够的忐忑,那些藏在谷糠与木箱深处的、不知如何言说的盼望,从来都没有被辜负。
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在我们生命里继续孵着,孵出理解,孵出慈悲,孵出一整个不怕寒凉的后半生。
凡所有标注为“来源:奉节网”的稿件版权均为本站所有,若需引用、转载,请来信获取授权,使用时请注明来源和原文链接,并在授权范围内使用;未经授权不得盗链、盗用本站资源、不得复制或仿造本网站、不得随意转载使用本站版权所有的稿件,若有违反,我站将追究有相关法律责任。
本站法律顾问:重庆夔府律师事务所 余世军。